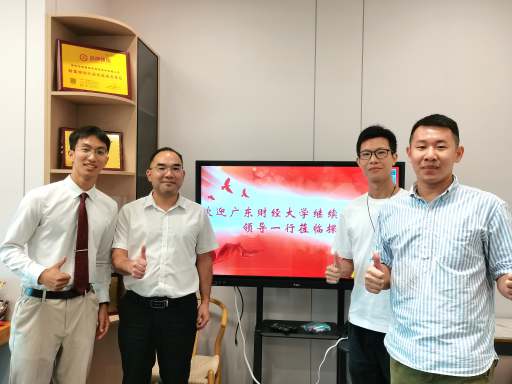关于汪曾祺先生,噢,还是称其为汪老吧。
汪老这一生,大致的经历在他文章中提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与老舍先生颇有交情,受他帮助不少。
许是师从沈从文的缘故,他俩的风格颇为相似,却又不全相同。如果说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如水,那么汪老的文字便如玉,温润如玉的玉。
写得出如玉般文字的汪老,大概也是一个自然纯净之人,用汪老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汪老不喜规矩,喜自然。这点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可看出。汪老的孩子偶尔喊他“老头子”,连他的孙女儿也开始这么叫。更有甚者,他让孙女儿往自己脑袋上缀满了小花卡子,末了还征求意见:“今天老头儿累了,赶明儿再玩!”,逗得人哈哈大笑。说实在的,汪老这辈人,能做到这样随性、不讲究辈分的真没几个。这不,汪老的亲家母对孙女儿的做法可是一万个不同意,认为孩子“没大没小”。但汪老却觉得,在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必须得先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而在小说《受戒》中,荸荠庵里的和尚们不守清规,明海也有了爱情,“打兔子兼偷鸡的”可“都是正经人”,这样的现象可谓是一反“常态”。只不过这种“常态”,指的是所谓的世俗常态。在汪老那个充满了人性与爱的世界中,这没什么好可耻的。在那个世界里,不会有任何人指责他们。因为汪老并不会指责这样的他们。
汪老的自然纯净,还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汪老的文字中充斥着大量短句,字句朴实,尤其在他晚年的创作中,很难找到斧凿痕迹。汪老在《小说笔谈》提到,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汪老的孙女儿十分嫌弃他的作品,觉得“不怎么样”,因为学校让她摘抄好词好句,可汪老的作品里“没词儿”!汪老听了,哈哈大笑,说:“没词儿好!”毕竟汪老最反感那些所谓的“抒情散文”了,因为他总觉得:“这么大的人了,有话不好好说。”
汪老这一生也创作了不少小说,小说创作绕不开“结构”二字,那么汪老是怎么设置小说结构的呢?
汪老说:“随便。”
跟旁人不一样,大多数人觉得散文是写生活,而小说是编故事。而汪老认为小说是回忆,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汪老的许多小说是没有太多情节的,常被称为“散文化小说”,大多数时候都像在谈生活,平淡、简单,就算故事有时不太符合“常态”,却也让人觉得十分真实。《受戒》也一样,除了末尾那一段,受戒的故事算不上有情节,简直是纯粹叙事生活的小说。
关于汪老的创作,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便是他关于吃食的创作。汪老谈吃是真的好,谈得活色生香,是文字版的舌尖上的中国。我也是个馋人,总是跟着汪老的文字食指大动。我不爱吃咸鸭蛋,但也能被汪老撩拨得馋涎欲滴,于是对高邮的咸鸭蛋久久不能忘怀。汪老说:“筷子头一扎下去,吱——— 红油就冒出来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美食能治愈人,汪老笔下的吃食也是能治愈人的。但他偶尔也会回味一下:“这些老店现在都没有了。”实在引人唏嘘。
汪老极少为抨击什么,教育什么而去写作。他是位无论在哪儿都能发现美,并由衷感叹:“真美啊”的作家。一个人得到什么程度,才能如洗尽铅华般自然通透呢?汪曾祺先生,无论是为人亦或文字,都是我极崇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