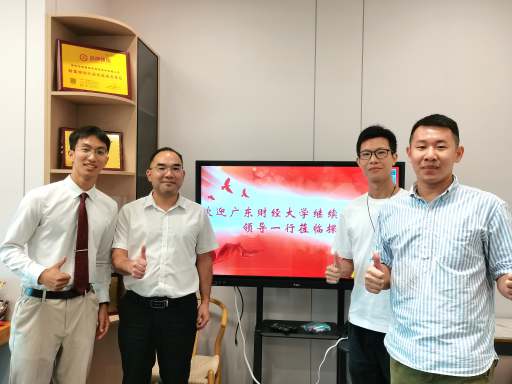春,就这样落了下来。
五点多接近六点的广州,天将亮未亮,有一层老旧默片的年代感。我挣扎一夜未眠,好友说,自己出去北校区走走吧,很舒服。她或许说的是空气舒服,又或许是说那无人环绕的清晨,抑或说她自己往日的一份心境,一切都在“舒服”这个词眼面前,愈发地入味。
一路空旷。因为学校树木多,从出门时便一路都得以闻到小鸟们的叫声,叽叽、喳喳,长短不一地抒发着,像在高声说着什么话,却又极为飘渺,可能因为声音漂浮在空中的缘故,于是夹着清晨的凉意,有了一种春的宁静。
因为是春天,满枝的绿意蔓延,每棵树都挺挺地往上生长,不高,枝桠繁密,有另外一番老者的意味。之所以说老,且不仅仅是因着这繁密,更是因着满地堆积的落叶,从空中簌簌然下滑,风一吹就四面地飘动,打在路人的衣物臂膀上,有时还落在孩子的摇篮车里。
你永远不知自然造物的机密在哪,能在广州的四月里,同时见到满地飘落的黄叶和满树的绿意,这本身就是一个清晨的冲击。环卫的阿姨叔叔们总是很早就起身,在大家的脚印还未踩过的校道,他们提前亲吻了南方。扫帚是竹编的,很大,因着风吹日晒而褪去颜色,染了污渍,在阿姨瘦小的手下挥舞着,树叶翻腾像中了女巫的咒术,术语延绵整个春天。
我们的学校建在一个城中村里,这个地段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处在所谓的灰色地带中。往日里走的两道大门都没有明显的界限,男女老少皆可往来,出了校门便是繁乱的街市,各色各样的人物随风飘零,公交车穿梭,电瓶车穿梭,也没有所谓的红绿灯界限,车子经过的时候靠人来判断开和停,人经过的时候靠心情来判断走或留,竟也一切井然,很少有所谓的交通喧闹。
但是过到另一面便不同了,从学校现在的后门,未来不知何时可以建起另一大门的那一处走去,眼到之处皆是层层叠起的高楼,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每年人山人海的广交会,一切自由而充满机会的地方,一切渺小的自我,都将在晨烟笼罩的南丰汇下,成为历史的尘埃。
“如果有天堂,那应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的这句话最近赫然出现在学校图书馆的宣传动画中,四月是一个读书月,每个人都在进行所谓的诚心的朗读,却很少有人愿意去亲近一个默默无名的清晨,除了那些为了温饱的环卫工人们。我们的图书馆与琶洲会展遥遥相对,另一侧面则相望广州塔,在每个喧闹的夜里,广州塔五彩斑斓的灯光和生硬的大字广告,都深深打在了这座不是很美的图书馆身上,而里面白灯通明,每一个角落里都藏着理想的声音。
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的图书馆少了人气,变成一个静默的中年男子,沉着而无言,自对天空而立,不依托。看着对面早起练习发声的稚嫩学生,草坪上轰轰作响的割草机行驶,新的一日又来临了。
四周围着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小树。不比前面的茂密,更多的是单薄而孤立的个体,于是我突然想到,每个人来到世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事件。它们是可以这样的:有一棵树满是嫩绿的叶子,在它的隔壁则是完全干瘦的枯枝,但又不是快死了,而是即将爆发新的生命。所以一切向死而生的事物,都是从小树长成大树的,它不可能变为一只鸟,也不能变成一朵云,但可以生长千年,甚至更为久远,长长久久地生长而旺盛着。
树下是路,偶尔有几个人跑步、散步、踱步,老人家一对两对地出现,懒洋洋地走着打着节拍。有人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人民公园。至于说的那个人是谁,在这样一个清晨,是定然引不起任何人去考究的兴趣的。鸟的叫声越发清脆,甚至因为树叶少,还能看见它们在眼前飞,拍打着小小的翅膀。附近有一个空地,规划建设综合馆,未建的空地上面成片地开起了野花,因为地的中间泥土堆积而高过人头,上面又长满植物,给人以漫山遍野的遐想。
在这样一个单独的时刻,远离了家乡,在这个充满反感的城市里,我独自一人,第一次有了“希望这一生长一点”的念头,哪怕在过往悠长的二十年里,它只属于昙花一现,但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里,却已然足够让人倍加珍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