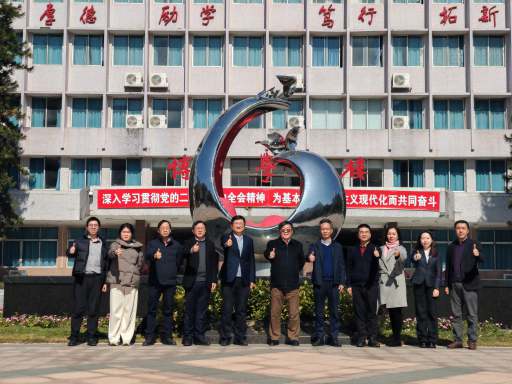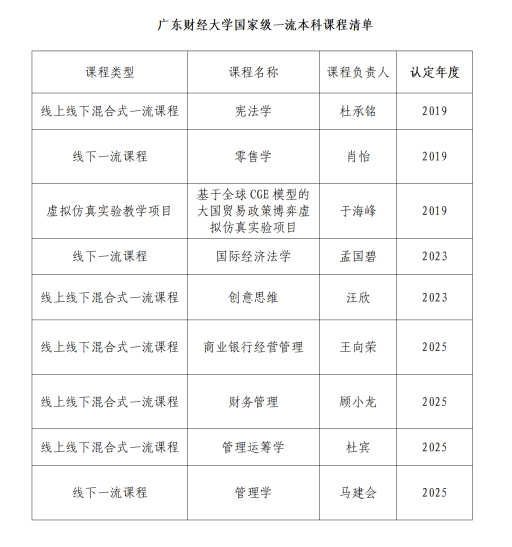某一个平常的日子,摄影博主鹿道森卖掉了自己的摄影器材,留下一封遗书和一句“无需为他立碑,只愿玫瑰年年为他盛放”后便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校园霸凌与家人的缺席萦绕的曾经,鹿道森已无力再去治愈。从什么时候开始,“活着”这件事又变成了一个难题呢?
张艺谋改编自余华小说《活着》的同名电影,讲述了旧时代阔少爷徐福贵这一生关于“活着”这一命题的探索。电影同样有张艺谋惯用的大场面,也有张晋《芙蓉镇》中的那种昏暗压抑的色调。相比小说,电影显得更加温情,尤其结尾是福贵家珍在阳光柔柔照射着的小房间里逗馒头玩这种一家子和和乐乐的场面,就像梦一般。
因为贪赌把最后一院房输掉了的徐福贵拉着生病的老母和一车子坛坛罐罐上街卖,放不下架子的他愣是一分钱也没赚。因为心灰意冷一度离开了福贵的妻子家珍抱着男婴有庆回来了,夫妻二人决定做点买卖过安生日子。福贵去找龙二借钱,龙二给了他一套皮影,救急不救穷。某天,当皮影班子唱得正热闹的时候,福贵和伙计春生被抓去当壮丁。这里多次运用俯拍的视角,仿佛在诉说生命的渺小无力。
战争结束,百废待兴,对于福贵却是一段又一段失去的开始。
深夜里福贵回到家,才知道老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凤霞一次发烧给烧成了聋哑人,她看着福贵,露出了世上最干净的笑容。
学校要求学生炼钢,福贵背着有庆带着满满一盒的饺子。没想到有庆累得在墙后根睡着了,区长倒车时正好把墙撞倒了,区长正是战友春生。福贵夫妻二人就在这平常的午后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后来每年祭奠有庆时,夫妻俩都在有庆坟上放一盒饺子,而最爱车的春生再也没开过车。
一个晚上,春生最后一次找福贵,家珍这次也终于为春生打开了门,但是春生不得不离开了,家珍喊着:“春生,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你可得好好活着。”
最后,春生消失在了黑暗中。
到了凤霞谈婚论嫁的年龄,镇长介绍的万二喜对凤霞一见钟情,福贵家珍回家看到万二喜和凤霞画墙时正笑着看着对方。正应了那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爱情在物质缓慢的流速中得以保留纯粹和长久。
不久,凤霞即将生产,大家发现医院里都是一群年轻小护士,唯一的老大夫因为一下子吃了七个馒头把自己撑晕了,凤霞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痛苦死去。
福贵虽然没有背负什么使命,也没有阶段目标任务的设定,但是“不断失去”贯穿了他的一生:财尽散,失骨肉,亡战友,饱忧惧……最后福贵家珍已经能笑着调侃当时被撑晕了的老大夫,这时会突然意识到,一切释怀都是曾经最疼的伤口。
如果说一个英雄要完成拯救世界的任务,就必须献祭伙伴、牺牲父母增加仇恨值以及交换自己的自由,那么将这种模式套到福贵这一小老百姓身上似乎太过沉重。他的一生不算波澜壮阔,只是和平常里的无常作斗争,只是填补无常带来的伤痛的代价太大了。
虽然如此,作品本身不是控诉一个时代给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它只是在思考,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能发挥“活着”这件事多大的可能性。历史长河不仅是史书上记载的一个个伟人的挥斥方遒,更是一个个简单不过的人出于对生命最崇高的敬意和守护而接续的桥梁。
正如《天堂电影院》说的:“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苦。”人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愈加复杂,但未必会随之变得坚强,与“活着”的信念感并存的是“脆弱”的本性。因此我们会寻找一些寄托,或者降低对生活的要求,但是又不愿去尝试,因为前者是天真,后者是苟且。“活着”只是对人生最低的要求,对“活着”司空见惯于是有些鄙夷,很多人也忘了这个信念已经作为灵魂的一部分曾伴随一代又一代人走到如今。
所以活着,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