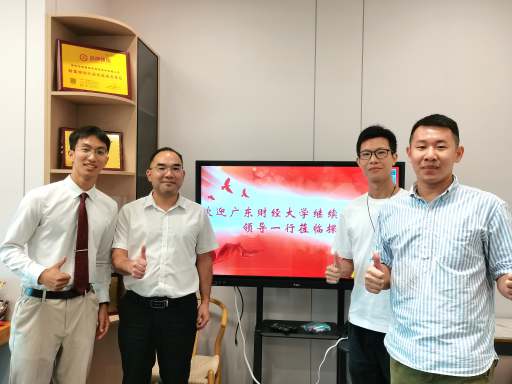如果不是因为考试,兴许未必有机会邂逅南京。孩童时已听闻这座城的厚重,但是我与它的距离从未拉近。
南京很冷,冷得很萧瑟。梧桐树的枝丫间剩下零星几片叶子,大风刮得路上的人们裹紧棉袄直往屋子里跑。到南京时正值清早,走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都是些老人家,他们簇拥在早餐档前,身影在炊烟里若隐若现。本匆匆忙忙的他们买完后,却会悠闲地坐在青石椅上,慢慢地剥开包装,将食物送进口中。
沿大街走去,很难见到青年人,破旧的老楼下是谈笑下棋的老爷爷,沏上一壶龙井,逗弄鸟雀,便是一早晨。朝天宫红色的宫墙外,随处可见嬉笑的孩童,一孩子穿梭在宫门前的草木间,老人在后头气喘吁吁地追赶着,爷孙俩在阳光下化作一道剪影,融在朝天宫斑驳而又威严的墙中。
成天游荡在城里,不知不觉走到了秦淮河。天色渐黑,河道逐渐被笼罩在黑夜中,顷刻间河畔楼房便被灯点亮了。靠在河边石栏上,眼前是似被金黄的灯光推着往前行的画舫,还有两岸连着的一排又一排徽派建筑下坐着喝酒吃饭的游人。行人不绝如缕,大多都像我一样,驻足在河畔,听着那桨声,看着那如水墨画般的黑白建筑。此情此景总觉似曾相识,不知是在杜甫的七绝诗中呢?还是朱自清的行文中呢?
夜慢慢沉了,河中流水似凝结一般将各色灯光揉杂在一起,只见得黑乎乎一片。画舫上的游人慢慢散去,水面上的涟漪一波一波往外延,缓缓消融。我并不似其他游人,倒是在桥上不愿离去。岸两边梧桐树轻轻摆晃,我不禁将手塞入口袋,视线里闯入了一只摇摇晃晃的画舫,舫上有一对夫妇,估摸着是船家,丈夫坐在船头,妻子站在船尾,他们与许多急切收拾舫上物品的船家不同,其动作好似一幅升格的画面:丈夫坐在小木椅上,一呼一吸间伴随着烟气的消散;另一头妻子仔细地将包裹着糖浆的野果插入木签。画舫渐行渐远,暗黄的灯光将船映在青黑的河水中,六朝古都的风韵尽溶在这秦淮水里,其实这繁华之后只是凡间烟火罢了。
南京的夜,较晨时更为惨淡。荡了一天,终究因脚底生疼放慢了速度,大脑却并未放慢节奏,始终思量着能否沉浸在古人赞颂的金陵夜色里。归路上立在我头上的总是墙漆脱落,外墙破裂的老楼,伴着那没有生机的梧桐,总觉着夜晚的南京褪去了古都的高傲,露出的是内里苍老破败的心。半路上,直觉身旁一股肃杀的气息扑来,转头一看,是一栋巴洛克式的建筑,铁门紧闭,铁锁上满是锈迹,铁门后立着两根石柱,可惜上面的浮雕早已被大火抹去,楼体上尽是烟熏后的黑迹。定睛一看,印刻在大门上的是曾经象征着最高权威的青天标,标下大字更是撼人。光绪年间已有的交通银行,如今林立在我眼前,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直视,权因越与它接近越能听见南京的悲鸣罢了。
我点起一根香烟,坐在马路牙子上,脑中思绪万千。路上零零散散地只有年事已高的老人,提着鸟笼,拎着茶壶往家里缓缓走去。其实,那座破败的银行即是南京的缩影,曾是象征高贵,却被历史的车轮碾过,洗尽铅华后又与凡间烟火相合,容下无数平民百姓,城里再也没有肃杀与威严,取而代之的是龙井香气或是鸟雀叫声。但没变的是那六朝金粉,那傲骨嶙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