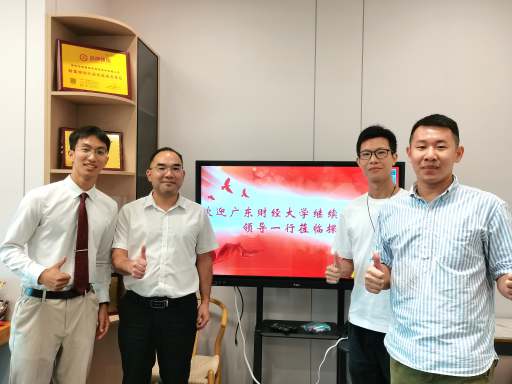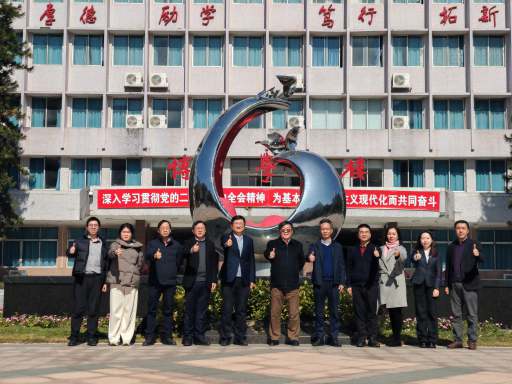在温差并不明显的南方城市,四季的轮转是以特别的人事来区分的,雨丝细密的是春季,围炉团聚的是冬季。而我感知夏季的到来,却是用味道来明晰的。
最先让我感知的,是花露水的味道。在我看来,味道各有它的重量,而花露水无论浓烈,总是轻飘飘地浮散在空气里,让人想起游曳在池塘里的、不过手掌大小的金鱼,轻捷机敏。冰冰凉凉的味道瞬间把我拖入榕树绿色的阴凉里,这种廉价且大众的香气弥散在竹席上的一个个夏季里。童年昏昏沉沉的午后,半梦半醒之间,蚊子轻巧地飞走,我只好翻身坐起,抓过花露水细细的瓶颈,胡乱地涂在脚背上。奶奶用蒲扇扇动的风混杂着花露水的香气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花露水的香气,在我的记忆里被赋予了奇异的安全感。
还有一种稍重的味道,就是荷花的味道。一朵巴掌大小的饱满的荷花苞被一片片拆开,粉嫩的花瓣与花蕊莲蓬,一同铺在白瓷壶底,只要倒入开水,就是一道可口解暑的夏饮。《浮生六记》里,沈复的妻子陈芸会在夜晚把茶包好,放入荷花花蕾中,等到第二天清晨再取出,泡好的茶会有荷花的香气。荷花的香气甜蜜绵长,混着雾露的水汽,总让人想起莲子的糯,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茶适合与它同饮。少女的我多少有些矫情,总挑剔荷花只能配冰糖,因为冰糖比白糖清,我的母亲也不厌其烦,总会准备好冰糖。
夏天最重的味道,是更难以琢磨的暑气。干燥的地面在太阳的炙烤下散发着滚烫的泥土味,贪婪地向着更空阔的四面八方蔓延,直至攀升墙上开出火焰似的石榴花。石榴花低垂着褶皱的正红色花瓣,在四溢的喧闹蝉声里,像极了吉普赛女人跳弗拉明戈时的大摆舞裙。我匆匆路过操场,鼻腔里满是辛辣的味道,恨不得马上回到开着空调、凉风习习的教室里,一是怕中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暑气,二是为了把那份高考冲刺一百题做完。
三重味道,组成了我的夏天,和我一路走过来的时间,是我在季节轮转里留存在身体里的记忆。每年夏天到来时,它们总会提醒我:这是你的时间。
时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或者,准确地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像数学一样明晰,连人也不是。人只知道走完自己的时间之后会死亡,而不知道如何去记忆自己的时间,于是人们发明了季节。可惜我生活的地方,连季节也无法明晰地划分。一个夏季,最终被我用不同的味道分割,刻印在身体里。当它的气息窜入我的鼻腔,充满肺叶,随着心脏泵动血液流向大脑,唤醒神经深处的记忆时,我的身体才告诉我:又是一个轮转了。
可惜对我来说,琢磨时间并不是有意思的事情,我更喜欢琢磨比时间更“真实”的东西,比如花露水,比如荷花,比如斑驳树荫下小小的石榴。我喜欢琢磨石榴上肥硕慵懒的虫子,它一动不动,说不定也是热坏了。时间里穿行而过的人事,那些细小的趣味,比时间有意思得多。
所以,只有当我开始琢磨花露水的味道时,夏天才到了。
今年的夏天开始在思修课室里。我坐下,嗅着花露水的味道,发现了面前的女孩。她戴上耳机,高高的马尾轻轻扫过脖颈,露出一片发根处的柔软的绒毛,几颗粉红的痘痘显眼地缀在白皙的皮肤上。她纤细的手指搭在肩上,指甲涂成淡淡的水蜜桃的颜色。
那时我想,这位不知名的少女,大概就是我今年的夏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