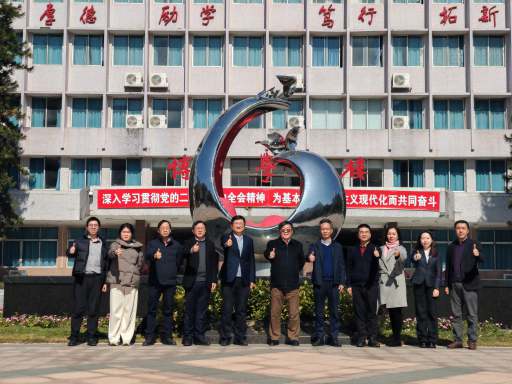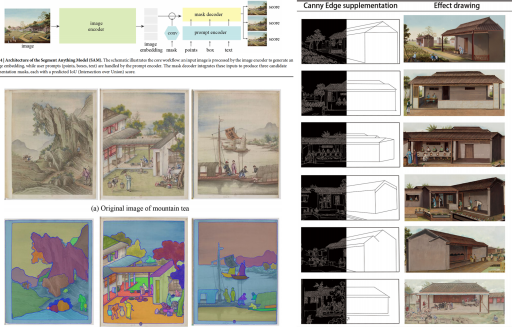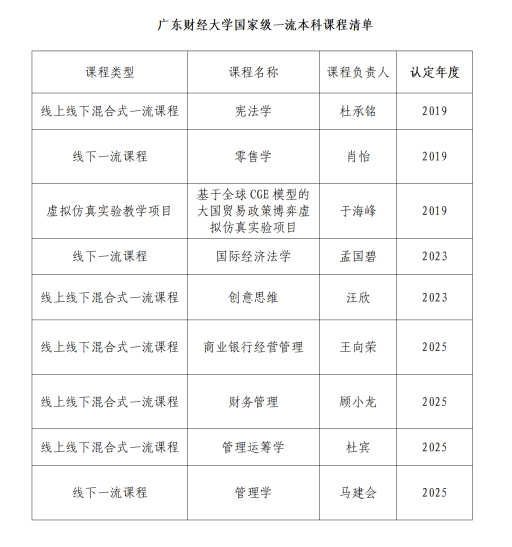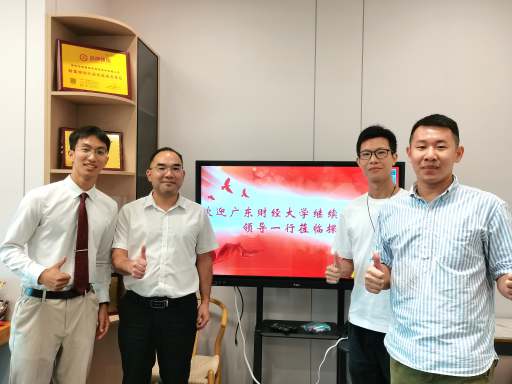打工文学从萌芽到壮大迄今30年,从珠三角的嘈杂厂房一路走到国际大奖的聚光灯下,但关于打工文学的话题一直争议不断。羊城晚报特辟出专版,举办研讨会,持续不断地予以报道,希望能引起主流文坛的关注。日前,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羊城晚报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宣传部、人文与传播学院承办的“打工文学30年”论坛在广东财经大学举行。研讨会由羊城晚报副刊部主任陈桥生、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江冰共同主持,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
各抒己见
蒋述卓 【广东省作协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打工文学”的概念一直在变化
有的作者是很愿意被称为打工作家的,但是有的就不愿意了,他们认为这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应该把社会学里的“基层”这个概念移植到“打工文学”里来,用“基层”来概括“打工”,把“打工文学”的概念扩大,这样它包含的东西就更多了。“基层打工”把大学毕业生、公务员乃至创业者都包含进来了。
“打工文学”的概念是在延伸的,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因为打工写作者本身就一直在变化,他写的内容、精神状态、文本层次都在发生变化,逐渐逐渐比以前增强。以前的打工写作者大多是从自尊出发写作,他是站在一种阶级对立的角度来写作的,这类打工者在作品里都非常仇视他们的老板。后来,有些打工者开始思考自身的命运,思考自己的生活。比如说郑小琼的一首诗,写到女工在嚼甘蔗,说大家嚼完了甘蔗以后就把它吐了,她在这里写道:她们吐掉的是她们自身的青春。我觉得她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也有一些打工者后来变成了小老板,他们非常了解打工者的感受,所以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属于“打工文学”。还有一些打工者上升到了管理者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愿意回首打工的这段痛苦经历,所以他们转而写乡愁,那么对于这类作品,单单用“打工文学”已经不能概括进去了。
所以“打工文学”的概念是在一直变化的,因为打工者一直在变化,他们的价值追求,理想都不一样了,从生存追求上升到享受追求。他们要表达的文学诉求也完全不一样。现在你再回过头去写打工者和老板之间有多大的冲突隔阂,已经没有用了,这种血泪控诉已经没人想要看了。
另一个方面,随着打工者的追求层次的上升,整体素质的提高,“打工文学”整体水平也在提高。而且现在随着有金融能力的人介入打工阶层,打工者的构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许多人因为兴趣而开了电影工作室、咖啡厅、酒吧,人们称之为文艺打工,还有北漂。这些打工者的层次是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把“打工文学”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打工文学”诞生到现在三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长,它在某些方面的文学成就丝毫不比其他传统文学差,甚至有超越的部分。毫无疑问,“打工文学”将在文学史上留下灿烂一笔,而且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有更新的面貌。
总之,“打工文学”是一种现象,但是只要底层存在,“打工文学”就会一直存在,只是概念发生了变化,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来代替它,或许到了那个时候,“打工”这个概念已经被淡化了。
郭小东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
“打工文学”缺乏共同主题的大爆发
“打工文学”从一个比较原始到后来完成了一个爬坡的过程,实际上这也证明了“打工文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历史的命名,它应该是文学史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昙花一现的一种概念,而不是永恒的概念。它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内涵,然后我们要不断地重新命名它,但现在还可以看到像上世纪90年代末那种比较幼稚的写作和表述。
打工群体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也不是无产者。为什么知青文学可以成为一个体系,而打工文学不可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两个群体之间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知青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打工者是有产者,而且还构不成阶级。打工者在农村里有自己的地,有房子,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资产,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城市接受这种漂流者的身份。
所以,在90年代末20余世纪初,农民工进城以后经历了被原始资本积累剥削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们跟夏衍笔下的包身工、鲁迅笔下那些被剥削的农民是没有区别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文学史现象,没有必要把他们浓墨重彩地推出来,然后强调他们的悲惨的背景。我也写过小说,也知道如何在小说里表达自己的那种内心的痛苦,不管是当知青也好,打工也好,对于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一段或者光荣或者耻辱的人生经历,区别只在于他是否成功了。
知青文学和打工文学之间有很多很明显的壁垒。“打工文学”的背景是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是无组织的,散漫的,是资本积累和流通过程中的一个自发的行为。它不是一种运动,没有纲领没有政策,没有号召,没有领袖。打工者是自由的,没有严密的组织。比如说,家里有人去当了知青,那是牵肠挂肚心里痛苦的;而现在家里有几个孩子去打工那是有收获的,是期待的,期待你把钱寄回来。虽然造成了一些留守儿童,造成了他们失去教育的机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但对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来说是向前进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知青作家是在控诉,在发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打工文学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打工者个体内心的诉求,缺乏一个群体性的对于某个共同主题的大爆发。
江冰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打工文学”还没受到足够重视
江冰:“打工文学”和80后新媒体其实都有一个共享的基础,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娱乐多元化的格局以后,肯定这方面的读者没有以前那么多,但还是有一些读者;这些读者对于创作的推动,以及所形成的热潮,肯定随着文学的黄金时代的过去而消退。
美国青春学者对于中国80后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年轻人不会采取一种过激的行为,总体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温和一种是表现在虚拟环境中,还有一种就是通过青春写作来表达。“打工文学”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也是这样,就是有了这样一群打工者,然后他们有精神诉求,然后他们又有消费者,然后他们要努力在社会中发声,其中有一批人要通过“打工文学”去顽强地表现自己。尤其在当下,文学成为一个重要的宣泄渠道,打工文学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在发声。
中国的城乡差别开始出来以后,城乡之间开始了流动,大批农民开始涌进城市,并慢慢发展成为“农一代”、“农二代”、“农三代”。他们的消费心理和价值追求也慢慢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代人赚了钱以后肯定是要回家盖房子的,第二代往回寄的钱就比较少了,第三代就希望留在城市里了。这样一群变化着的人要表达他们变化着的诉求,那么“打工文学”也就势必要被推着向前发展。打工者的形象会不会一直是《国家订单》里那样子,我想是会变化的。
中国现在有一种城市边缘人的状况,他们有着身份焦虑。大批从乡村涌进城市但是无法融入城市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精神诉求。这群城市边缘人又造成了乡村边缘人,就是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那么这些留守儿童来到城市,接触到城市以后又会怎样去评价农村和城市?所以今天的“打工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应该说在主流文坛中,“打工文学”还是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广东文学史上,有两个文学现象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一个是“打工文学”的诞生,一个是90年代的女性写作。他们都对中国文学史起着微妙的推动作用,但是文学史上对于他们的记录都是非常单薄。
众声喧哗
3“打工作家”:身份的焦虑?
江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打工者是底层的,底层他不具有承担文化基因这个责任,但他们确实要发声。其实他们的身份焦虑比知青要更强烈。当知青已经成为主潮的时候他们有那种优越感,但是打工者缺乏这种自信,所以他们今天要改名说他们是“新产业工人”。
王十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身份焦虑这个是理论家给我们的,别人说我们要做新产业工人,不是我们自己要的。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打工作家”这样的话,我认为这就是我身上的一个胎记。我身上长了个胎记,我要到处去炫耀说我长了个胎记吗?用不着。那我又要回避我身上的这个胎记吗?也用不着。这就是我的感受,我不拿我的打工经历来炫耀,也不去回避它。
任何文学的命名都是阶段性的。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给自己去分门别类,给他自己做限制,不会说我写作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一个知青作家、我是一个打工作家,肯定不会这样想。我就是在写作。我不会说因为我是一个打工作家,我就去写打工的生活,不会因为我是一个知青作家,我就去写知青的生活,我,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一块的生活所以我就写它。多简单的一个事。
柳冬妩【广东省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现在谈“打工文学”特别的困难。因为“打工文学”的概念并不确定,概念是一种假定的前提但是又很难有标准答案。就像文学的概念一样,古今中外多少学者都没人能给文学下一个标准。“打工文学”、“知青文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问郭老师什么是“知青文学”他可能也很难解释。
郭小东【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我可以很准确的告诉你。详细到它每个阶段的特征和代表人物,你承不承认是另外一件事。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有些概念的形成有时候只是一种现象,而且这些现象离开了它的历史背景马上就消失了。知青文学之所以可以经历那么多个文学阶段是因为这一代人集体面对一个共同的命题。这个命题它不单是一个文学命题,它还是一个政治命题。
所以一个客观的文史学家他应该是负责任的,去处理好这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盲目地给它命名。
田忠辉【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主任】:关于打工文学的概念,这是理论家的问题,作家不用关注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宽松的。就和文学的概念一样,都是演变着的。打工文学也是这样,文学的类型有种“家族相似性”,只要是与打工题材,打工主题相关的都可以属于这个范畴,这都是可以的。
身份焦虑肯定有的,郑小琼读很多书,为什么读书?读哪些书?干嘛要和你说,这就是一个身份焦虑的表现。其实,任何一种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诉求在里面的。
王燕子【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主任助理】:中国人的传统,名不正,则言不顺。在给打工文学正名的过程中,就是文学发展的过程。
2评判标准:立场或文本?
江冰:一种文学无论它生产什么样的东西,像巴尔扎克,他的作品描写的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那么一群人,这么一群人中肯定是有那么几个是作为文学典型留传下来。这是文学史评判的一种标准。要说打工文学,像这种文学典型恐怕还没有。但是像郭金牛《纸上还乡》要表达的那种具体情境下的某种情绪,我觉得是已经到了一种极致。
农民工和大学生毕业出来以后打工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来自农村。农民工确实是非常弱势的群体,这种属于弱势群体的卑微的心态他们一直带着。这种身份焦虑还是跟知青完全不一样。
郭小东: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长期以来就有这种阶级分析,或者是基层这样一种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观点是很可笑的。它是虚妄的。我统计过“文革”前我们把一个人的家庭成分划分了等级,起码有59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各有各的非常准确的政治待遇。
蒋述卓:我觉得评价一部文学作品还是要看作品本身的质量,不能看作者的立场。既然是文学,他就应该是以文学作品的水平来评价,而不是依赖于某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你所属的阶层高看你或者低看你。文学要有文学的标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文本。
王十月:打工文学历来就被人家认为是粗糙的。其实,当代文学基本全都是粗糙的。特别精致的文学反倒不是文学了。举个例子,杜甫活着的时候,他是一堆人的粉丝,是李白的粉丝,是别的作家的粉丝。但是杜甫在他活着的时候,在盛唐,大家不认为他是一个大诗人。在他的时代,那些诗歌选集里他是选不上的。杜甫死了51年后,元稹出来了。元稹成为文坛领袖的时候读到了杜甫的诗,这才给他编了诗集,写墓志铭,把他捧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大家公认杜甫的代表作是什么?《三壕三吏》、《秋心八首》,《石壕吏》,写的是什么:“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这不就是口水诗吗?在他活着的时候人家也根本不看。我经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唐诗没了李商隐会少了一抹斑斓的色彩,但是如果没了杜甫,我们的唐诗的高度要大打折扣。当时人们对杜甫的作品的评价是:粗糙,同样的问题放在我们当代作家的身上也是这样。另外一种是流行于中国的“擦边球”文学,他们常以审美的名义,遮蔽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逃避生活和现实的矛盾,也因此掩盖了作家思想的匮乏。所有的擦边球文学在中国的评论家那里都会被冠以“深刻”,而所有正面强攻现实的中国文学,得到的都是“粗糙”二字的评价。
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写的精致的文学,这些作品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实大家都是粗糙的,但是打工文学它在粗糙之余有大家没有的一些东西。
郭小东:“粗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指文字粗糙,还是指表达生活的层面不够深入,停留在一个相对较浅的水平?
田忠辉:应该叫“粗粝”,不应该叫“粗糙”。那是文学真正有生命感的东西。用美学的概念,这其实就是感性,这是冲击僵化的东西。是文学最本性的东西,是生命力的表现。
柳冬妩:“打工文学”首先在广东出现,涌现了一大批作家。现在回顾这30年,像林坚、王十月、郭金牛这些作家,他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他们是紧跟时代的文学潮流的,丝毫不因他们是打工者而落后。而且“打工文学”自身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除了纯文学以外还有许多通俗文学的类型。非常多元,非常丰富,不能一概而论。只是现在还是有人对“打工作家”存在偏见,望文生义,以为“打工作家”就应该是缺乏文化知识和文学修养的。
3后打工文学:何去何从?
柳冬妩:“打工文学”会比“知青文学”持续得更久。“知青文学”当年是几千万人,现在打工者有几个亿,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到现在远远没有完成。举个例子,东莞的户籍人口180万,流动人口有1000多万。那么这些人将何去何从?从文学上讲,就必须追问这些人将来到哪里去?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世界文学史上做横向比较,和现在中国同样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在当时出现了什么样的文学?法国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大量的描写纺织女工的文学作品,这和当时巴黎出现大量的乡下女孩到城市里做纺织女工有关;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南方与北方》等作品;美国在19世纪末期产生了芝加哥诗歌,诗人桑德堡写的诗和我们现在的“打工诗歌”是相似的。还有《嘉莉妹妹》,嘉莉妹妹在鞋厂描写的场景跟我们现在的打工场景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辛克莱的《屠场》,和我们现在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我大量阅读了卡夫卡的作品之后,看到有一些东西唤起了我的共鸣。后来我锁定了他的《变形记》,我把它跟“打工文学”做比较,当然这有争议。卡夫卡没有站在打工者或者是老板的立场,他更多的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去写作,这和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里面做的处理有某种相似。卡夫卡所在的地方是当时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就像我们现在的珠三角,有大量的乡下人来到布拉格这一带。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变迁带来人们的情感结构的变迁,社会现象导致了文学现象的产生。
王燕子: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因为它的虚构性的存在,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文学和历史的区别在于,作家不但能写过去发生的事、现在发生的事,还能写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刚才讲到如何直面现实的问题,一个是正面强攻,一个是打“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什么?是它没有反映现实呢,还是反映得比较隐晦?
王十月:我的小说全部都是虚构的,但是它的精神肯定是真实的。我写我们基层的困境,生活的困境,这些肯定是真实的。
王燕子:当时有人谈你的作品时提到一个生存写作与写作生存的关系。这就是讲的一个真实性。到底什么是真实性?你进入到那个在场的时候,你是在展现它的细节真实性。但是这个真实的细节你可以提炼出来,而且你的作品也在表现这个。问题在于提炼出来这个真实是当下的真实一个部分,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部分。能不能更往后走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后打工文学要走到哪里去?
田忠辉:现在打工文学被关注的时候,都还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身份焦虑这些。把卡夫卡文学放到打工文学的平台上来说,是把人性的高度拉低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当然焦虑了,你后面虽然还是把这种焦虑性提到人性了,不过,这种方式肯定把研究外国文学的那些人气死了。当然,我们对于文学的研究可以是多角度的,这也是一种开拓方式吧。
文/陈行杨
(羊城晚报2015年7月19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