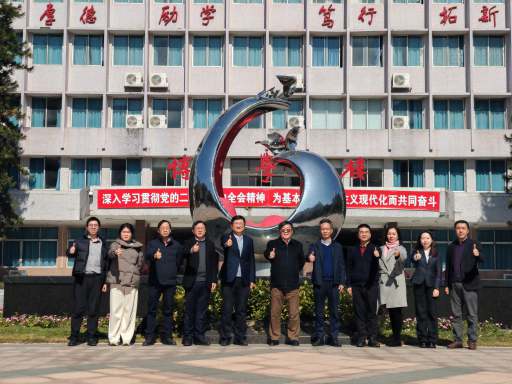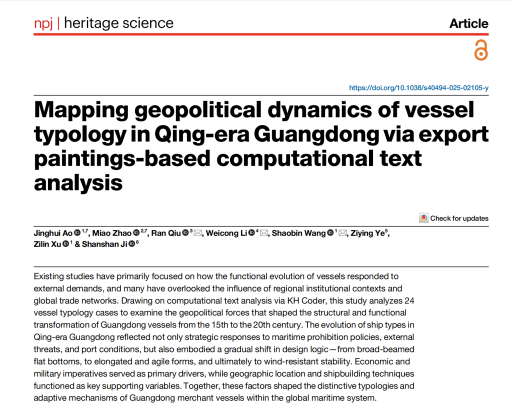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爷爷倚在藤椅上,摇着蒲扇,嘴里念着“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问爷爷:“爷爷,你在说什么呀?”爷爷没有回答我,将眼睛闭上,仍然摇着那把蒲扇。我抬头看爷爷,一缕一缕的阳光从晦暗的窗帘透进来,顺着蒲扇斑驳的沿路,爬上爷爷那张苍老的脸——那是我第一次在爷爷身上发现岁月的痕迹。
听爸爸讲,爷爷是个很聪明的人,喜欢读书。但是爷爷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的父母负担不起沉重的学费,让爷爷早早辍学务农。爷爷刚开始放牛的时候,一手拿着书一手牵着牛,边走边读。我想那幅画面该是某个夏天的清晨或者傍晚,有一个晴朗的天空,一位少年在乡野中走着,身后跟着一头牛,少年的眼睛紧紧盯着手上的书,眼神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求——太富有书生气了!可是爷爷出生在一个生活充满苦难,理想难以实现的年代。 爷爷再也没有时间捧起他的小书,他被人嘲笑:“那么爱读书,就去考个大学!边干活边看书,像什么样子嘛!”每次爷爷回忆起这段来自隔壁生产队一个姓杨的妇人说的话时,都气得牙痒痒。因为印象太深,所以爷爷至今还记得她姓杨。
爷爷读书的习惯,一搁置就搁置了大半辈子。爷爷的房间铺满了零散的报纸和书籍,浓郁的书尘味飘浮在房间里,就像爷爷那段被荒废的青春岁月的挽歌。爷爷爱读《道德经》,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爷爷房间正中央挂着一副很大的自己写的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爷爷没有学过书法,字体写得歪歪斜斜,但仍然孩子气地坚持要挂上去,爸爸只好服从,特意定制了一个木框将它裱了起来,一挂就是十二年。我看这副字,也看了十二年。它像家人一般,即便不了解,却也习惯了它的存在。
我开始不懂这句话,直到初二的一堂语文课上,老师将这句话翻译给我们听,那种感觉,像突然从一个做了很久的童年的梦里醒来。我想到爷爷房间里的那幅字,想到爷爷。“狂风不会整天地刮,暴雨也有终止的那一天……”老师仍然在讲台上讲着,而我却望向窗外的天——天空灰蒙蒙的。
爷爷身体变差仿佛就是在我上完那节语文课不久。奶奶因为疾病,离开得早,只留下爷爷一人。爷爷要么一个人在房间读他的书写他的字,要么在阳台的藤椅上打盹。虽然有我们每天在家里陪着,但我总觉得爷爷是孤独的。半个月过去了,爷爷肺痨加重,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初三,靠着爷爷坐在病床的床沿,爷爷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回答说《傲慢与偏见》,爷爷不知道这本书,告诉我还是多读老祖宗的东西比较好。
于是爷爷又和我谈起了《道德经》,“我最开始读老子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爷爷让我不要随便和其他人起争论,要沉住气。他还跟我说:“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我小时候教你读过的,‘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爷爷摸着我的头,叫我别总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别总把自己搞得太困难……我静静地听着,愈发感到惆怅。爷爷其实很了解我,很知道我的个性,但爷爷从来不指责我。从前我和爷爷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和父母吵架,哭着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关上半天后泪眼婆娑地走进客厅,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沉稳地像一瓶水,静静地陪着我,不说一个字。今天坐在病房里,爷爷却将他大半生所读到的都告诉了我。我和爷爷隔了两代的距离,但此时此刻,我仿佛去到了爷爷放牛的那个清晨或傍晚。我同爷爷一起,陪着他在时光的轨迹上缓步前行。
爷爷通过阅读回到了他的青春,人却不再是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我看着爷爷那副黑框的老花镜,镜片厚得如同一块瓦片,在松弛的皮肉间缓慢地向下推移。想到爷爷平凡又普通的一生,因为我爸的缘故在晚年享了几年福,可那段年轻时被夺去的日子,却无论如何也回不来了。爷爷跟我讲人生、讲《道德经》,何尝不是对那时的自己、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的一种补偿呢?我若是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爷爷也许会开心很多很多。
我最后一次去病房里探望爷爷,病床上的爷爷羸弱地缩成一团。当晚的凌晨三点半,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连带那些他告诉过我的《道德经》里的句子。我只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整理爷爷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陈旧的书籍。《道德经》排在书架的最前面,扉页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爸爸将墙上的字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框面。我透过透明的玻璃看到爷爷亲手写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像见到一位阔别已久的老朋友,泪珠无声地流淌下来。爷爷选取这句话作为他人生的信条。在奶奶离开后,在身体变差后,在经历了无数次对过去那段岁月的深情缅怀后,爷爷选择相信这句话,也选择相信《道德经》。
在爷爷去世后的几年,我的人生开启了转折与加速。家庭的纷争和学业的压力在我身上堆积,加上我自己性格的缘故,在无数次几乎要放弃挣扎的时候,我总会想到爷爷。爷爷和我说的那些话,每次都会化作柔软羽毛包裹住我那尚不坚硬的心房。后面我读了越来越多的书,总觉得爷爷是“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而我自己也越来越喜欢《道德经》里面那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也许在以后的人生里,我会面临和爷爷同样的抉择,遭遇爷爷所经历过的一切。好在我是幸运的,爷爷在七十岁的时候才能亲手写下“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而我在二十岁就能够主导我的命运。《道德经》陪爷爷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程,我又从《道德经》里孵化出一个全新的自我。
怀念爷爷,怀念那段爷爷给我讲《道德经》的日子。
(本文乃《中国文化典籍导读》课程思政教学成果之一,指导老师:人文与传播学院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