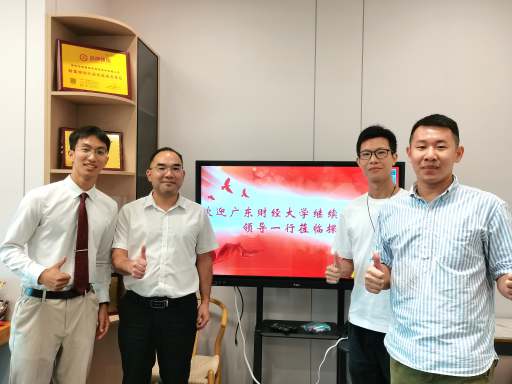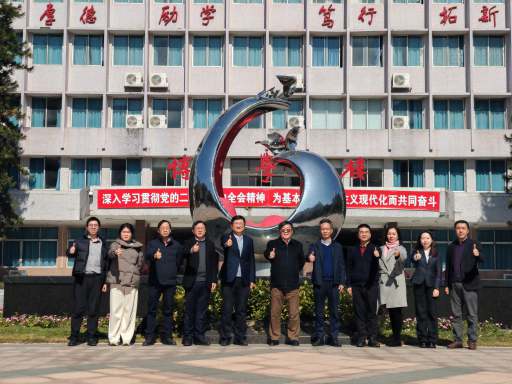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理念先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重大论断实现了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管制到“上下共治”的双向奔赴,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群众受管”旧有模式,指向的是“多元共生、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治理新生态。
一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嬗变、利益诉求的多元分化、风险挑战的叠加交织,仅靠政府“单打独斗”已力不从心。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战略回应——它呼唤每一个社会细胞、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成为治理网络的活性节点。
这一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再到党的十九大擘画“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直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升华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思想脉络清晰可见: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参与程度日益深化,利益联结日益紧密。
“人人有责”是身份重塑,强调明确各主体的社会责任,唤醒沉睡的主体意识;“人人尽责”是行动赋能,强调社会各主体之间权责明确,激发协同的治理动能;“人人享有”是价值依归,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成果享有的全面性,锚定公平的成果分配。三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循环的生命体。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迭代升级,形成了强大政治影响力和理论话语影响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提供了科学指引。
什么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大家的事情大家定,是为共建;大家的事情大家干,是为共治;大家的事情大家评,是为共享。用广东话讲就是:“一条村一条心,一个社区一个煲,煲乜嘢料、加乜嘢辣,放几多火候、落几多盐,都由大家一起话事!”
二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市场主体参与热情不高、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不足、公众个人参与的内驱力有待提升等原因,我国在社会治理具体实践和主体关系格局中呈现出“党委和政府为主,市场、社会与公众为辅”的局面。
以基层治理为例,本应需要群众共同参与,然而在一些地方,“干部干、群众看”现象突出,甚至演化为“干部干,群众看,干的看的都抱怨”。一边是社区苦于人手不够,一边是居民即使没事干也不愿参与。
由于政府长期扮演“全能管理者”和“保姆”角色,民众则被定位为政策执行的“旁观者”或“受惠者”;政府与民众之间不是合作型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种单向度的治理结构导致社会参与乏力,公共事务成为政府的“独角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这告诫我们,新时代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建设者,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合力的实践者。社会治理没有旁观者,谁都不是局外人。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向——公民身份从“治理对象”变为“治理主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同的“当家人”格局。
从“旁观者”到“当家人”的主体跃迁,本质是治理哲学的范式革命——将“人民至上”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当每一位个体都能在共同体中找到存在感与获得感,社会治理也升华为“美美与共”的治理图景。
三
传统社会治理机制常被诟病为“单向度”——以行政权力为唯一驱动轴,政府如同一部带有精密齿轮箱的抽水机,将社会需求拆解为标准化任务,把社会问题吸入、过滤、处理后单向输出“标准答案”,不必考虑他者感受与公众反馈。
这种线性的、以行政命令为轴心的制度模式,在风险单一、诉求同质化的工业社会曾显高效,但却在网络社会和信息时代的“高并发”社会风险面前日益捉襟见肘:政策脉冲与民意波纹错位,部门壁垒与数据烟囱并存,治理结果看似“完成”却难以“完美”。
事实上,过往社会治理的“单向度”呈现,难以满足民众诉求的“颗粒化”爆发,难以适配城乡差异和代际分化,更难以破解公众长期被定位为“治理对象”的症结。治理终章,就如同一条笔直却狭窄的高速公路,车越多越堵,最终把“共建共治共享”的愿景困在匝道。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根基在“人人”。如何唤醒沉默的大多数,将一个个“你和我”等单向度的人唤醒,变为“我们”的共同体,是“生态圈”能否落地的关键。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下的“生态圈”,是对“单向度”的范式革命。其核心在于通过发挥多元共治的“光合作用”,构建“共生型制度生态”。“生态圈”的功能,使得不同主体能在治理实践中彼此成就,完成从机械流程到有机生态的“基因编程”,实现“一核多样”的“有机共治”。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离不开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态圈”提供了前提。
发挥党建引领,使治理主体由“一元”扩展为“群落”。党组织如同“磁石”,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吸附凝聚成治理合力。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众不再是“主—客”关系,而是共生节点。
推进制度创新,使治理规则由“刚性”迭代为“弹性”。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既包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顶层设计,也包括经过基层群众反复协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还包括诸如“清单制”“积分制”等地方探索。法律、政策、自治章程等既相容共促,又协同演化。
强化技术赋能,使治理数字由“垂直”演变为“环流”。电子居住证、一键报事报修、AI识别高空抛物、打造“数字居委会”、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数智技术在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大显神通,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数据像水一样在土壤、根系、叶片之间循环,滋养每一环治理决策。
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成为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中国之治”就会在每一盏灯火、每一声问候、每一次回望里热气腾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给出了“恰到好处”的答案。
(南方杂志于2025年11月4日报道链接:https://www.nfzz.net.cn/node_a514f1b8e1/5757a66255.shtml?r=0.18958318921177864)